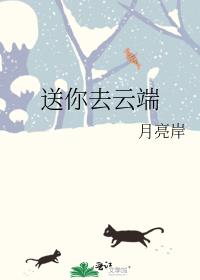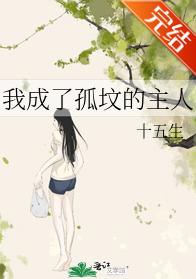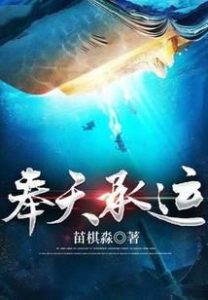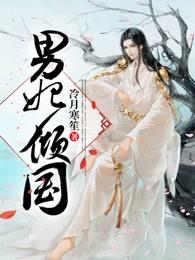話說,
撫院打發列吏部起身後,也怕劉公公怪他,随即就把一夥人犯題上去。
道:
敲梆喝號者仁傑,傳香者實貴,打死随從者顏富,成如,向念。
又去央求江實寵致封書信與吳二寶,求他能從輕發落。
這江實寵也是個有些慈心的人,這些天聽說拿住了這起人,自己也不過意,又見已亂了蘇州,打死了孫掌家,覺得蘇州撫院如此處治百姓,不妥。
說道:
都是我造的罪孽!
遂連忙寫書函星夜進京去求情。
劉大鵬聽見激變了蘇州,心中也覺得慌張,後又接到撫院的本,才知已調停了。
便喚吳二寶來商議說道:
蘇州濱湖近海之地,人民撒野的地方,如若株連殺戮,恐致民變,況且江南是漕運重地,不比他處,不如就依樣葫蘆,從寬些吧!
劉大鵬遂便假意做了個人情,只批将為首五人立決,其餘送有司嚴緝。
又于本上批道:
段過令該撫提拿解來京,錦衣衛官校即刻撤回。
且說,
吳江禦史可造,初任湖廣武康縣時,官清如水,決斷如流,才守兼優,聲名大振,經撫院交章題薦,後改任了浙江仁和縣。
這仁和縣是附省的首縣,政務繁冗,民俗淳厚。
可造就任後,辦事精明,立法極簡,審理詞訟,任你有錢有勢的來請托走關系,他概不容情,并無冤枉,征收錢糧,任你多頑梗,他都會設法追捕,合縣百姓都呼之為青天。
平常可造稍有閑時,便下學訓課士子,藹然一堂,如若再得餘閑,便或與鄉之賢士大夫逍遙湖上,或偕德望父老,訪民風于四野。
所以,
士民德之,及六年,奏最行,任為禦史,合郡為他建祠。
不料,
卻莫名其妙為徐牙濤所劾,說他侵蝕郡縣庫帑,坐贓削職,令撫院追回充饷。
此時,
合縣缙紳都為他到蘇州撫院衙門面禀毫無此事。
撫院遂含糊答應而退。
後又有浙江與本處生監百姓紛紛上具呈保留,為他分辨。
撫院才只得面谕說道:
如今官員坐贓,概不能辨,一時也搞不清楚,如若略微追贓少了些,便就會與參本上的條款不合,裏面肯定就要拿問,這豈不是反害了禦史可造了嗎?此事本院并非不知道這是個冤枉,也并非就不想委曲保全,但是不認贓不問罪,上面是不肯停止的,我看,還是認了倒可杜後患,諸生等的此呈,本院就只好存之,以彰厚道!
衆人聽後,也知道撫院此言近理,也想不出其他還有啥子辦法來,就只得俯首而回。
不多幾天,
又因江實寵論劾了本翰林士晉進京。
這兩地的百姓都憐他沒處叫屈,聞聽蘇州有打校尉的事件發生。
其中有仗義的說道:
蘇州人都有俠氣,我們杭州人咋個就獨無人心麽?可爺此去,我們雖不能擊登聞鼓,為他伸冤,只是說他坐贓這麽多,将咋個抵償哇?我看這事必要致害他一身,并累及妻子,不若我們就為他捐合些銀兩替他完了贓,雖然救不得他的罪,卻也可免他妻子被追索的破家之苦。
話畢,
便先是有幾個人岀名寫帖子。
通告滿城人等道:
前在本縣可造大人父母官,六年仁德,恩惠在民,今遭誣害,坐贓數千金,家道清貧,力難完帑,凡我士民,各懷仗義之心,可各量力樂意捐資,共成義舉!
蘇杭兩地士大夫見百姓如此倡議。
也相議道:
小民尚知,如此仗義,我輩豈可獨無心?
便見有幾個紳衿人士出來為首。
內中也有悭吝的拖延不出,衆人也就惡極,遂聚合衆公面議,要求照家私分派,分上中下三等,這樣就不怕你不出。
其餘那些生監酸子,雖然所出都有限,卻也積少成多,又有本縣大戶和鹽當店,都各出十兩五兩的相助。
又有一等過往的客商也說道:
我們自從可爺在任,鈔稅雜差,一些都沒有擾過我們。
說畢,
也岀財相助。
又有衙門各役,也感恩可爺一味愛民,不肯縱容他們索錢害人,卻從未曾風打亂敲過一人,沒想到如今受此冤屈。
遂吏書門役也都各人以貧富派銀,也有在工食上扣支的。
百姓們多在城隍廟建醮,祈保生還,又設櫃在大殿上書簿捐錢,以資可爺完帑。
來往燒香的士女,或一錢二錢,三分五分,十文五文,都親手入櫃。
每逢朔望一合并,統計共不下數十金,這都是江浙之民,感恩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