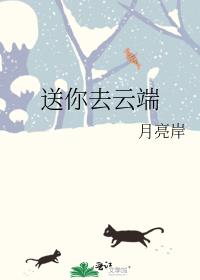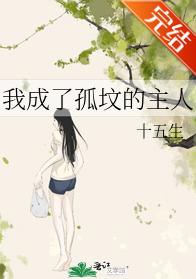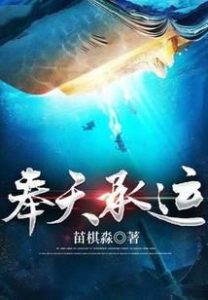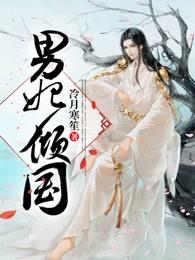更新時間2013-10-2 21:53:59 字數:1396
1923年他回湖南,在小吳門附近的清水塘22號住了很短時間,6月又要赴廣州。9月至12月,他又回湖南從事dang的工作,年底奉上級通知由長沙去上海轉廣州,準備參加大會議。她挽手相送,他強抑感情,賦詩安慰。
《賀新郎·別友》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
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
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
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
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似臺風掃寰宇。
重比翼,和雲翥。
家事與國事的難全,使他不得不從“有情”的夫妻恩愛中不時抽身離去,并因此引起婚姻生活的小小波瀾,比如1923年底離開長沙時發生的“誤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別友”命名那闕詞。也就是說,他不僅把她當作妻,也當作友,所謂“算人間知己吾和汝”,用意當在求妻之相知。其實,仔細體會,《賀新郎》一詞是充滿悲情之味的。兩人之間的“誤會”或許僅在兩人之間有些許意義,放在整個歷史發展中看,不過如過眼雲煙罷了,實在細微不足道。他的心不能完全放在家中,他胸懷的是天下蒼生,為了偉大的事業,他只能做出“揮手從茲去”的決定。可是此去堪稱絕決,卻也算得灑脫嗎?面對愛妻的“苦情重訴”和“熱淚欲零”,他如何才能說服自己義無反顧地遠離而忍心讓她獨自承受生活之重負?他沒有覺得自己的選擇是錯的,而求妻之理解的言下之意就是怪她“不夠知己”。
其實,他也知道,行走天涯的孤旅是不好受的,但這不足以成為他貪戀家室之樂的理由。他滿懷着“希望”,這才是最重要的,而所謂“希望”,卻是與溫情脈脈的夫妻恩愛迥然不同。那麽,他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妻子理解“昆侖崩絕壁”和“臺風掃寰宇”的劇烈慘酷是出于不得已呢?他沒有說。也許,正像他日後所謂的“人間正道是滄桑”所暗示的,必然之事物是說不上有情無情的,對于“天地不仁”,連他自己都無能為力,只能暗懷希望而已。“重比翼,和雲翥”只能是希望之語。人有病,天是不會知道的,因為“天若有情天亦老”,而天是永遠不老的。他沒有等到希望中“重比翼,和雲翥”的那一天,她也沒有等到。
這闕詞中婉約與豪放并存,響亮的尾巴并非做作而為。但“要似”之類的語句不是命令,而是希望。他對未來帶來的天翻地覆景象的“希望”卻又是在“憑割斷愁絲恨縷”的“決心”之後,好像确實從反面證實了“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俗語。問題是,這首詞最後還是回到了“兒女情長”。希望之後還有希望,也許是最終的希望,那就是“重比翼,和雲翥”。魯迅曾言: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死,而是為了讓人生。那麽,他的這首詞是否有意表示,革命不是為了斬斷“兒女情長”,而恰是為了更好的“兒女情長”。
魯迅有詩雲:“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随着一個尼采所謂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時代的到來,世人肯定會越來越重視歷史人物的情感因素,即便其可能因被低俗的眼光打量而顯得是軟綿綿、溫吞吞的,但關注偉人的個人生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偉人有同于常人的一面,但也正在這些尋常之處,可能顯出不同尋常的偉大。不過,魯迅在詩中所言之“情”似乎更多地指“天倫之樂”。
可是,1927年,他率軍上井岡山開辟根據地,發現很多危險,組織上考慮他的安全性,安排一位槍法厲害的女保镖給他,日久生情,他以為她死了,同時考慮到自身安全,與女保镖結婚。而此時,她正在韶山從事革命工作,號召民衆團結起來反對壓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